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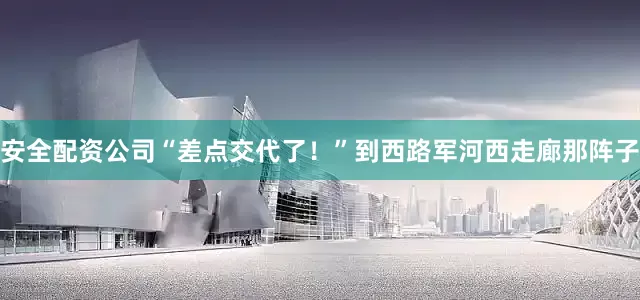
38军三位师长抗美援朝实录:杨大易、江潮、翟仲禹,谁的“少将”更难得?
有时候,历史像一锅老火汤,总得慢慢熬。38军的“三驾马车”,每个人身上都有点不一样的味道。你要说1955年评衔那会儿,怎么就杨大易一个人挂了少将?这事儿搁现在都有人念叨。
四川苍溪那个小山村——白山乡车子村,春天泥巴地里种玉米的时候,小杨家门口总是冒着炊烟。1919年4月的一天,他呱呱坠地。他妈常说:“咱家穷归穷,你要争气。”结果,这孩子真争气——14岁扛起红缨枪,说走就走。当通讯员、班长、排长,一路打进川陕苏区。“六路围攻”时他跟着部队在山沟沟里转悠,有时候鞋底磨破了,就用麻绳捆脚板继续跑。
长征途中,大雪封顶,他裤腿冻成冰棍,还背着命令往前冲。有回夜里冷得直哆嗦,他摸黑找块石头坐下喘口气,一颗流弹擦过耳朵,把帽檐崩掉半边。他拍拍脑袋,“差点交代了!”到西路军河西走廊那阵子,同伴倒下一个又一个,他心想:“不能死在这鬼地方。”熬过来了,也记住了一辈子的兄弟情。

抗战爆发后,被派去山东沂蒙山区教新兵操练。“别光看书本,会钻壕沟才算真本事!”他这么吼学员们。日伪来扫荡时,他们躲进高粱地,等敌人靠近再一窝蜂冲出来。有一年冬天冻疮烂脚面,也照样带队打游击。他自己悄悄塞几块煮红薯给伤员吃,“别声张啊,多吃点补补。”
解放战争东北那段日子,从松花江边一直杀到广西丘陵。他指挥335团啃硬骨头,有一次天津城外夜袭,美军防线灯火通明,他蹲在土堆后嘀咕:“今晚必须拿下,不然全盘皆输。”渡江战役更刺激,只七条船横渡滚滚长江,对岸炮弹呼啦啦砸下来,那场面至今让人心跳加速。“拼吧!撑过去就是胜利!”
1950年秋末风刮得脸疼,第112师被拉到鸭绿江边。一听命令,要守飞虎山!敌人的坦克轰隆隆开上来,小伙子们饿极了啃树皮也不退缩。这仗五昼夜没合眼,下雨泥浆灌满鞋,全团剩下一千多人还死守阵地。有个士兵晕倒前嘴里还喊“万岁”。松骨峰阻击战又是一场硬仗,一个连只剩7个重伤号还趴在那里扣扳机。这些细节,每次讲起来我都觉得鼻尖发酸。

反观113师和114师,那也是各有绝活。河北定县出生的江潮小时候喜欢写字,可惜家境拮据早早辍学,当兵去了东北军当文书。据说他爹是赤脚医生,经常免费给乡亲看病,这股善良劲后来也留到了部队。不巧母亲早逝,继母对他一般般,所以小伙计格外能吃苦。在57军混出名堂,被送去士官学校深造,再后来投奔八路,在滨海独立旅干营长、团长,把日伪整治得够呛。有次带海陵独立团反扫荡,人手短缺只能靠计谋取胜,“兄弟们跟我来!”喊完第一个冲出去。
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中表现突出,但最经典还是第二次朝鲜战役“三所里穿插”。70多公里泥泞山道急行14小时,全程没有一句怨言,到达目的地比美韩联军快一步,把退路卡死,让对方措手不及。这一招太狠,为38军赢足脸面。但结局嘛……1955年评衔时资历稍浅,只能先拿大校。不过1964年终于升为少将,也是熬出来的结果吧!
再看看翟仲禹,小名叫翟家乐,是山东济阳仁风镇的人。从学生运动一路闯进八路阵营,在东北111师搞秘密党务工作。1942年的起义把不少旧部拉入革命怀抱,说起来很传奇但过程肯定惊险无比。当114师带队南征北讨时,每场恶仗都没落下,比如滇南红河桥头断敌退路,还有湘西剿匪四个月消灭千余土匪,这种耐力和胆识不是谁都有。

朝鲜第一到第四次大战,以及52年的嘎日岭奇袭,都让114师声名远扬。一晚上端掉几千土耳其旅士兵,还能全身而退,不容易啊!不过呢,人家参加革命时间晚一点(1938),土地革命时期没赶上,所以评衔轮不到优先权,也是挺无奈。
其实1955年的授衔制度很讲究资历与职务双保险——正儿八经正师级基本就是大校档位。如果你是老红军或者功劳特别突出才能直接提一级。所以同样都是抗美援朝里的猛将,因为参战年份不同分数线自然差异明显。
回国以后,各自的人生轨迹也蛮有意思:

- 杨大易调任42军参谋长、副司令,再做桂林步校校长龙岗几年,然后湖南辽宁两省当司令直到退休;晚景安详,据说女儿媳妇都很贤惠;
- 江潮身体不好,高原肺结核折腾好几年,不过依然坚持工作多年,到南京高级陆院做副校管训练;临终葬于雨花台;
- 翟仲禹则去了苏联军事学院镀金回来后搞参谋和政治委员工作,一直忙到80年代才歇下来,据传脾气耿直但待人宽厚。

三个人物性格迥异,但拼劲十足。如果非要问我谁最值得佩服,其实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各有不同。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细枝末节的小动作,比如严寒中裹破棉衣蹲壕沟喝凉水,又比如急行70公里累瘫还互相搀扶,还有黎明前静静听见自己心跳声……
偶尔翻这些故事,总觉得时代变迁太快,如今我们习惯舒适,却忘记他们曾经负重前行。不知大家有没有哪位亲戚或邻居曾经历类似苦难?或许哪一天饭桌上一句唠叨,就是历史留下的小尾巴吧。
内容来自公开史料与个人见解,仅供学习交流,不构成历史定论。
旺源配资-网上在线配资炒股公司-加杠杆怎么炒股-温州股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